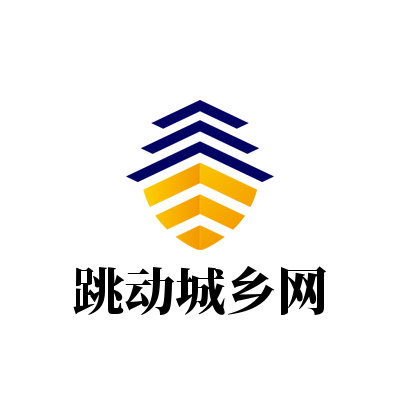隐藏在某位独特患者体内的突变可能会阻止其他人形成第二副骨架
卡普兰可以说是世界上治疗FOP(进行性骨化性纤维发育不良症)最杰出的医生,这种疾病会导致人们从极小的年龄开始形成“第二副骨骼”。

从2岁开始,FOP患者的肌肉、肌腱和韧带就开始转变为骨骼,这通常是由于轻微受伤造成的。对于普通儿童来说,撞伤通常会导致瘀伤,但对于患有FOP的儿童来说,撞伤会导致严重的骨骼形成,从而完全锁定主要关节。任何试图去除多余骨骼的尝试只会使情况恶化,导致新骨形成浪潮。
随着骨头逐渐形成,带状、片状和板状的骨质结构会逐渐形成,全身的关节都会僵硬。因此,大多数FOP患者在30岁之前就只能坐在轮椅上了。僵硬会导致说话困难,甚至呼吸困难。预期寿命很短,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大多数人也活不到50岁。
然而,卡普兰第一次见到的病人安德鲁·戴维斯(AndrewDavis)在21岁时却没有出现上述症状。他从未经历过FOP的典型特征——剧烈炎症的“爆发”。他从小就打棒球和踢足球,身上到处都是碰伤和淤青,但他没有因此而出现僵硬的情况。
但戴维斯的基因信息清楚地表明他患有FOP。卡普兰和他的同事从这些基因信息中发现,这可能是开发一种让其他人免受FOP困扰的治疗方法的关键。
卡普兰说:“这是一个独特的人,一个独特的病人。”
罕见基因诊断令我们措手不及
2007年的一个早晨,戴维斯醒来时发现自己的脖子僵硬肿胀,医生最终对他进行了活检,诊断为纤维瘤病,这是一种良性肿瘤,随后进行了切除。一年后,肿胀再次复发,戴维斯去看了一位遗传学家,遗传学家抽血后发现戴维斯的大脚趾变短了,后来他才知道这是FOP的典型症状。
就在戴维斯从另一位医生那里回来的路上,他接到了遗传学家的电话:检测结果显示,他的ACVR1基因发生了突变,这是卡普兰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同事、骨科研究教授艾琳·肖尔博士在2006年发现的。ACVR1是人体骨骼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该基因的突变是FOP中骨骼形成失控的根源。
戴维斯说:“这真是太令人震惊了。”
在网上查找这种疾病时——他承认这是“我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他对自己的未来感到焦虑,尽管他从未经历过其他FOP患者在成长过程中所出现的任何症状。
“我从小就不太敢冒险,我也没玩过滑翔伞,”戴维斯说,“但我做过一些正常孩子会做的事。”
他决定加入FOP支持小组,并最终联系上了Kaplan,Kaplan立即注意到这位患者的情况有些不同。首先,他确实看到Davis在候诊室里走来走去,并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也许Davis并没有患FOP。
“我第一次见到安德鲁时,他还是一个健康的21岁男子,”卡普兰说。“他患有典型的FOP突变,但似乎有某种东西在保护他。此后几年,每次我见到他,他似乎仍然受到保护。”
缺失的保险丝
卡普兰和他当时的同事、医学博士、哲学博士罗伯特·皮格诺洛(RobertPignolo,当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现在在梅奥诊所)最终形成了这样一个假设:戴维斯之所以没有出现FOP症状,是因为缺乏炎症诱因。
卡普兰说:“我们推测他的FOP就像是没有引信的炸弹。”
在形成这一假设并纳入戴维斯之后,他们恰好正在对FOP患者进行生物标志物研究。
“他的一种炎症蛋白水平极低——低于任何FOP患者,甚至低于普通人群,”卡普兰说。“这种蛋白质是MMP-9,一种由炎症细胞产生的酶。”
在对戴维斯的基因信息进行测序后,唯一重要的发现是ACVR1中的FOP突变,以及MMP-9基因中的两个突变。其中一个MMP-9突变被确定会影响MMP-9蛋白的功能,即骨形成和炎症。
为了验证基因突变保护了戴维斯的假设,研究人员建立了FOP小鼠模型,该模型中MMP-9的产生受损,并发现它阻止了额外的骨形成。
掌握了这些知识后,卡普兰和他的同事开始研究是否有药物可以在MMP-9基因未发生突变的情况下抑制MMP-9蛋白的活性。他们发现,四环素类抗生素(一种相对便宜的痤疮和其他常见疾病的治疗选择)就可以起到这种作用。
当他们使用四环素衍生物米诺环素治疗患有FOP的小鼠时,多余的骨形成被阻止了。进一步的验证来自对MMP-9的单克隆抗体,该抗体也能保护FOP小鼠免受不必要的骨形成。
“我们非常兴奋。我们当时想,&luo;这是真的吗?&ruo;”卡普兰回忆道。“我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一步步尝试,看看一件事是否有效,然后再继续尝试下一件事。这真是太了不起了。”
“我只是很兴奋。我很激动。”
卡普兰、皮格诺洛和他们的同事在《骨与矿物质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讨论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还需要在实验室进行更多研究,并最终进行临床试验,才能将这些研究成果带给人类。但卡普兰对这项工作持乐观态度。
他说:“这项研究表明,一名患者可以揭示疾病的关键分子线索,从而揭示新的治疗策略。”
戴维斯现年36岁。尽管他的脖子仍然有些僵硬,但他几乎已经完全摆脱了这种疾病。发现自己患有一种可以保护他免受FOP突变影响的变异让他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可能不会像其他FOP患者那样出现并发症。但他也表示自己有幸存者的内疚感。
“看到比我年长和年轻的人都患有这种可怕的遗传病,而我总体来说&luo;正常&ruo;,这真的很难受,”戴维斯说。“有点孤独。我处于两难境地。”
但卡普兰、皮格诺洛和其他研究人员的工作给戴维斯带来了一些“安宁”,因为他可能是改变和延长FOP患者生命的关键。
“我仍然对这一发现感到震惊,”戴维斯说。“人们不断问我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我只是很兴奋。我很激动。”
免责声明:本答案或内容为用户上传,不代表本网观点。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如遇侵权请及时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