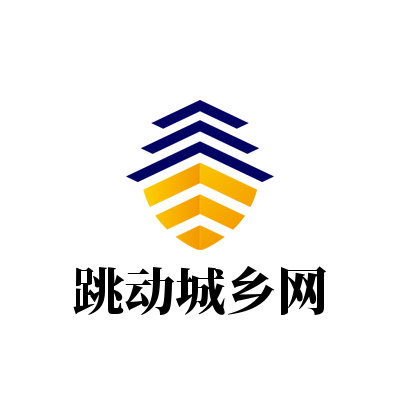由于围栏和道路标志性的稀树草原哺乳动物面临遗传问题
无论是阿滕伯勒、迪士尼还是国家地理,这个标志性的场景对很多人来说都是熟悉的。当成群结队的大型动物席卷非洲大草原、成群结队地跨过河流并被狮子、鬣狗和鳄鱼捕食时,大地在颤抖,尘土飞扬。

每年有130万头角马穿越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和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吸引了数十万游客,这一现象使塞伦盖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除了其雄伟的景观外,这种标志性物种的迁徙对于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也很重要。
不幸的是,这种大规模的年度迁徙现在只在非洲大陆的少数地方发现。在一些地区,道路、栅栏、农场和城市扩张破坏了角马群历史上的迁徙路线,使它们无法长途跋涉寻找新鲜的草和水。由哥本哈根大学研究人员领导的一项在《自然通讯》上发表的新研究表明,角马的遗传健康状况因此受到影响。
“没有人知道这会影响角马的遗传学。但我们的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不再迁徙但历史上曾经这样做过的角马种群的基因健康程度比那些继续迁徙的角马种群要差。这削弱了它们迁徙的机会。生物学系副教授、这项新研究的主要作者之一拉斯穆斯·海勒(RasmusHeller)说。
结果表明,非迁徙种群的遗传衰退反映在自然保护中衡量遗传健康的几个参数中。
该研究的第一作者之一刘晓东说:“不能再迁徙的角马的遗传多样性较低,基因更加孤立,而且近亲繁殖程度更高。我们预计这会导致生存率降低、生育力下降以及对健康的其他负面影响。”和生物系博士后。
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总体而言,这种标志性的稀树草原食草动物目前没有受到威胁。但从长远来看,无法再迁徙的角马群可能会变得更糟,例如,面对气候变化。
“长期的后果是,遗传多样性较低的种群应对环境变化影响的能力较差。它们的进化潜力降低了。因此,如果气候变化继续发生,它们的遗传变异就不那么大了一起努力适应——这最终可能威胁到他们的生存,”海勒说。
研究人员分析了从南非到肯尼亚整个分布范围内的121只角马的整个基因组。这是科研人员首次研究角马迁徙的遗传效应。
“因为我们研究了许多角马几乎整个范围内的基因组,所以我们能够对迁徙种群与非迁徙种群进行一般遗传比较。而且因为我们见证了多个地点之间的一致差异,所以结论很明确。确实,我们可以说,对于那些被阻止迁徙的角马来说,总体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它们生活在非洲大陆的哪个地方,”刘说。
规划中的公路和铁路走廊威胁着最后一次大迁徙
虽然角马的总数保持相当稳定,但许多当地的角马种群数量在近几十年来急剧下降,有一些甚至崩溃了。
一百五十年前,许多角马种群进行了大迁徙。然而,四十年前,非洲只剩下两次完整的角马大迁徙:著名的塞伦盖蒂马拉大迁徙和南部非洲卡拉哈里沙漠的一次。
“然而,特别是在博茨瓦纳,近年来人们竖起了围栏,以防止牛群与迁徙的野生动物接触。博茨瓦纳的卡拉哈里种群数量从1970年代的约260,000只下降到1980年代末的不到15,000只。所以今天,唯一剩下的大量人口是塞伦盖蒂-马拉地区。
该研究的另一位第一作者、生物系的米克尔·辛丁(MikkelSinding)表示:“但塞伦盖蒂-马拉迁徙也受到穿越该地区的公路和铁路走廊计划的威胁,这让很多人感到担忧。”
“作为一个物种,角马依靠迁徙来维持其庞大的数量。它们可以在常住的非迁徙种群中生存,但当它们无法迁徙时,它们的数量就会减少。例如,我们在其他地区的种群中看到了这一点霍恩海姆大学生物统计部门的高级统计学家、合著者约瑟夫·O·奥古图(JosephO.Ogutu)说:
“角马的迁徙使它们成为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因为它们的放牧可以保持植被健康,运输和分配养分,而它们本身则成为掠食者的猎物和食腐动物的腐肉。
“因此,当我们阻止标志性动物迁徙时,我们不仅会威胁到它们,还会威胁到许多其他物种。除此之外,我们还可能增加巨额旅游收入,使政府和当地社区受益。”
免责声明:本答案或内容为用户上传,不代表本网观点。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如遇侵权请及时联系本站删除。